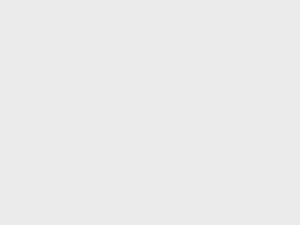- A+
 编者按
编者按在陈星汉的产品哲学里,游戏从来不只是寻求一时欢愉或者片刻逃避的娱乐。《风之旅人》正诠释了那句歌词,“淡淡交汇过,各不留下印”。
文 / 刘婕 本刊资深编辑
“人饿了要吃饭,渴了要喝水,但是如果人在情感上有饥渴怎么办?古代的时候,原始人绕着篝火跳舞,为的是获得情感上的安全感;到后来,古罗马把自然都征服了,将动物变成了牲畜,也没有了战争,此时人们反而因为缺乏危机感,而创造了斗兽场。”华人游戏设计师陈星汉如是说,“对于现代人来说,也是一样。”
2012年,索尼PSN平台上的《风之旅人》(Journey)令他声名大噪,这款不像游戏的游戏成为全球千万玩家情感体验的“朝圣之旅”,不仅创造了PSN上最快销售纪录,还在国际上获奖无数。而在今年9月,蛰伏了5年的陈星汉意外地出现在苹果公司的秋季发布会现场,带来了另一部颇具他个人“禅派风格”的作品。
在陈星汉的产品哲学里,游戏从来不只是寻求一时欢愉或者片刻逃避的娱乐。
眼泪是一个
重要的里程碑
“我们找了25个人测试这个游戏,有3个人玩哭了,我们才觉得这个游戏已经ready了。”

过于简单的游戏设定和故事叙述是《风之旅人》带给多数玩家的第一印象。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,电影般的长镜头掠过日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黄沙,停留在远处矗立的山峰——那便是终点。玩家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介旅人。
没有车、枪、球和眼花缭乱的道具,也没有复杂的游戏规则,玩家的形象对比其他游戏甚至算是“简陋”:一袭长袍,面无表情,动作只有方向与跳跃;身上一条类似围巾的装饰物,可以与这个世界里的布幡产生反应,积攒用于飞行的能量。而在两三个小时的旅途中,玩家或是在苍茫荒漠中漫无目的地行走,或是在光线暗淡的谷底躲避怪兽,又或者在水中解锁一个个机关,最后在山峰前的雪地艰难前行……
在任何一个时刻,都很有可能发现另外一个形象一模一样的玩家存在,无名无姓,不知男女,无法与之交谈对话,唯一的交流是单一的共鸣声。但是当双方靠近在一起时,便可以为对方的围巾补充能量。伙伴可能会陪伴一部分旅程然后消失不见,再次遇到的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;当然也会有一些默契时刻,两人共同经历快乐、恐惧、迷茫等诸多情绪之后,一起走完全程,抵达终点。
在许多游戏贩卖暴力、竞争、自由与强大的时候,《风之旅人》则一反常态,把“目的性”降到了最低。输与赢变得并不重要——游戏中的人物不会死去,所以不会“Game Over”,操作难度很低;没有强烈的奖惩机制——玩家可以积累围巾的长度,但只要坚持,就不会影响抵达终点的结局;遇到的陌生人不是竞争对手,而是相互支持的旅伴——并且只能在游戏结束时看到对方的名字。因为难度、功能和剧情保持着十足的克制以及类似留白的美感,又使它具备了极强的艺术性。
在陈星汉看来,市场上的太多作品强调使用力量击败他人、不断完成任务来获得心理的自我膨胀,《风之旅人》只是选择了与它们相反的情感,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相对世界的渺小与孤独,以便体会陌生玩家之间总是被游戏忽略的温情。学生时代的他就对游戏产业产生了这样一种认知:对比电影行业以情感来进行市场的细分,游戏这种较为年轻的行业仍停留在技术细分的阶段,而长久以来,市场上很难见到成年人喜欢的情感类游戏,能够做到老少皆宜的游戏作品更是少之又少。

14岁的时候,陈星汉在玩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时候哭了起来。“这部游戏是第一个让我感动到流泪的媒介。现在再回去想,我发现它肤浅而又老套。”但他承认,正这些眼泪让自己得到了安宁。
在制作《风之旅人》中爬山关卡的时候,陈星汉是哭着完成的;在内部测试时,他用玩家的眼泪来判断产品的成熟度;而在发布之后,更是收到不少有关哭泣的反馈。“你的情感被冲击到了一定高度,你会无法抑制地流眼泪。我会去追求它,因为这是作品冲击力高度的体现。只有你被冲击之后,你才会去思考这个作品的意义,才能记住这个东西。我希望我们创作的游戏被人记住,在这种情况下,有眼泪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。”
要做到强烈的情感冲击,陈星汉的团队在开发时采取了好莱坞式的叙事结构,以一种名为“统一神话”的故事架构建构出一个人的从青年到中年,从老年到重生的情感历程,再将其具象化到不同关卡,通过颜色、音乐、互动设计传递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情感曲线,来保证每个玩家走完“这一生”之后,产生类似焕然一新的自愈感。
让孩子感动很简单,但让成年人感动太难了,陈星汉感慨。“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成年人感动,就是创造某种和他们的生活特别相关的东西,或者创造某种东西,让它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可以带来力量。”
没有人一生下来
就是个混蛋
“所有的主机游戏都是关于互相杀戮……你没看到吗?是我们的游戏让我们变成了混蛋。”

在《风之旅人》的游戏论坛里,有不少名为“旅途的歉意”的帖子,内容是向游戏中遇到的匿名玩家的感谢和致歉——由于所有的相遇都是一期一会,两个玩家如果在旅途中失散,便再也不会遇到同一个人。“今晚我真心感激你的帮助。你在我没有获取飞行技能的时候如此地耐心。”“我很抱歉当那东西找上我们的时候我因为恐惧藏在了石头后面。它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”“我从没有想过要离开你,只是在跳跃的时候被猛地吹跑了。我想你。抱歉。”
在成年人玩的游戏中,不少是关于抢夺资源,完成任务,为此需要战胜其他玩家,甚至在对战中杀死对方。“如果你随机在网上遇到了一个玩家,将会是一段不良的体验。你认为他们会成为混蛋,是吧?但听好了:我们没有人生来就是混蛋。是游戏设计师让他们变成了混蛋。如果你把每一天都花在互相杀戮上,你又怎么能成为一个和善的人呢?”陈星汉说道。玩家的本性并不残忍,是系统让他们变得残忍,正确的系统能够挖掘人性中的善意。
而在开发过程中,他遭遇了自我质询和痛恨的时刻。开发团队早期提出了玩家相互碰撞的物理设定,以便一起通过难度稍高的关卡。但团队测试的结果却让陈星汉十分意外——人们并没有将相互碰撞的机制用于合作,却会将对方推下深渊,于是游戏的体验变成了人们聚集在悬崖边杀死彼此。“我们都知道这个游戏是关于人性的善,但还是无法抗拒要把对方杀死的冲动。”
一段时间里,陈星汉和团队因此陷入了情绪的低谷,而一位心理学家则向他解释了游戏中的困局:“第一次进入游戏的玩家就像孩子一样,他们是没有道德观念的,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坏,所以尝试那些给予了他们最强烈的反馈的行动。”
阻止孩子去做一件事情的方法,就是什么反馈都不给他们。团队将整个系统重新设计,玩家无法互相产生物理影响,只有通过吟唱简单的无意义音节来吸引彼此的注意。交互虽然简陋了很多,但达到了陈星汉想要的结果,玩家之间再无攻击性。
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游戏中,玩家可以通过收集布料来增加围巾的长度,储存飞行的能量,早期测试系统的机制是两个玩家同时发现布料时,只有一个人才能得到,以至于人们并不想要与另外一个人同行。之后,开发团队增加了一人获得布料,另一人可以跟着飞行的设定,玩家却还是讨厌第二个人的存在,感觉自己只是被对方利用了劳动力。最终,陈星汉决定去掉所有竞争机制,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,他们便会欣然接受彼此。

《风之旅人》最早的设定是一个四人游戏,它包含的社交要素更多,在趣味性上也会更加丰富。但对于陈星汉而言,他更痴迷于创造两个人之间独一无二的连接,额外多出来的两个人无疑会破坏它。团队曾尝试过游戏中常用的协作机制——拯救、治疗、一起开启一扇门……但陈星汉意识到,这些交流仍是机械的,真正的交流应该关乎情绪和情感。
“许多游戏让玩家处在任务解决模式,他们对交流情感没有兴趣。所以为了让他们准备好,我们不得不移除所有的任务和谜题。”他说,“然后我们努力让人们感到孤独。在这个精神层面上,玩家开始寻求连接,或者接近与他们想象的某人或某物。”
大多数情况下,玩家在《风之旅人》中都会经历飘摇起落、纠结反复的情感波动,而这种感觉通常与旅途中遭遇的伙伴有关——有人来去匆匆,不为所动;多数人却愿意在令人感到恐惧和绝望的关卡相互陪伴,在暴风雪中意外失散之后,在山巅等待对方的出现,一起结束游戏。对于陈星汉而言,玩家可以自行选择“个人主义”或者“集体主义”,不必感到任何压力,但相互陪伴的确是它的精髓。
虽然游戏中没有任何能够产生意义的沟通机制,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玩家之间有了这样一种默契——结束前,在纯净的雪地上为对方画一个心。毕竟,游戏可以随时重来,但再次遇到的,永远不是此时此刻的人。

游戏就是人生的隐喻
通过《风之旅人》,陈星汉完成了自身的一次蜕变。
陈星汉和合伙人共同创办的Thatgamecompany为《风之旅人》花费了3年之间,其中的一年,陈星汉在业余时间阅读各类社会学的书籍。由于索尼方面的预算十分有限,团队不得不将游戏的设定从森林改为沙漠,因为“需要画的更少”;原本丰满的人物形象也精简到最大限度——意外的是,这些却让游戏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美感。
在合约到期时,由于游戏效果还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情感成熟度,陈星汉曾向索尼方面申请延期,后者同意了这个请求,但并没有更多的预算支持,Thatgamecompany只好使用公司最后的一点经费完成了《风之旅人》的开发。2012年1月,游戏被提交给了索尼公司,1周之后,公司倒闭,原本12人的团队,只剩下陈星汉、首席工程师和首席设计师3个人等待资本和市场的“宣判”。
不久,陈星汉飞往旧金山,与Benchmark投资集团合伙人米奇·拉斯基(Mitch Lasky)会面,后者已经被这款游戏打动了,一周之后,Thatgamecompany获得了550万美元的投资。“我是个资本家,不是艺术赞助者。” 拉斯基这样说道,“他是个异类,在我们这个领域,异类才能带来最大的回报。我觉得《风之旅人》就是游戏行业里的《玩具总动员》。”起死回生后的Thatgamecompany依然保持小团队作业,总人数不到20人。
而陈星汉和他的团队也在3年里经历了自己“风一般”的起伏旅程。这样一款颇具浪漫色彩的作品,其开发过程十分痛苦。Thatgamecompany的前员工罗宾·汉妮卡(Robin Hunicke) 坦言,公司曾在制作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,包括签订了不切实际的时间表,还包括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,增加了成员之间的沟通风险;而贪婪也是公司曾走入的另一个误区,“我们总是眼高手低,反复迭代,但还是放弃了许多构思,有些的确也十分不合时宜。”在她看来,公司为此付出了极高的情绪代价,每个人都对彼此非常严苛,而企业文化也是外界无法想象的严肃。
在陈星汉看来,在创造一个全新事物的时候,由于没有参照物,免不了要碰很多次壁,他坦言,《风之旅人》一半的开发时间都在走弯路,包括新平台、新商业模式的挑战,也包括新的团队组合中管理上的诸多问题。
更重要的是,通过《风之旅人》,陈星汉完成了自身的一次蜕变——学生时代的他,还只是一个追求纯粹艺术性的开发者。这样一款反市场常态的游戏的大卖,令他创造出了一个艺术游戏的商业成功案例;而他自身作为一个经历过“末位淘汰”教育体制的竞争者,作品中却透露着一种深深的“无为”感,无论哪个,都是一种自我对立的有趣处境。

在《风之旅人》之后,陈星汉也开始负责商务和运作,作为Thatgamecompany的CEO,他现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商务上犯过的错误,但令人欣慰的是,人们对艺术类、情感互动类的游戏有了更多的认知,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,此类游戏也吸引到了市场上的投资人——而他的思路正是通过模仿早期皮克斯公司和迪士尼公司的做法,以一个现象级的作品来打造口碑。
与迪士尼类似,管理者身份的陈星汉现在正在寻找能把娱乐、想象力、创造力和工程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人——“情感工程师”,他这样定义,需要以自身的敏感度去把握一些微妙的情感,再通过程序创造出一个互动机制。“游戏行业太年轻了。如果要学习这个行业过去根本没有实现过的情感,你只能去其他类似的行业学习:戏剧、动画、电影、电视,这些是离游戏行业最近的,甚至主题公园设计也接近。”
接下来的陈星汉依然关注如何创造出能够引领情感的游戏,“这就是我为什么踏上这一旅程”。

本文全文刊载于《中欧商业评论》2017年10月刊
转载请联系后台
点击“阅读原文”订购本刊